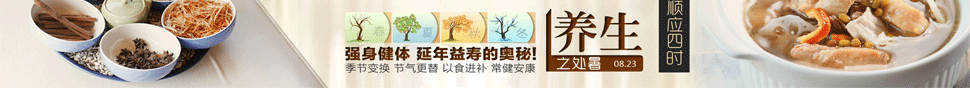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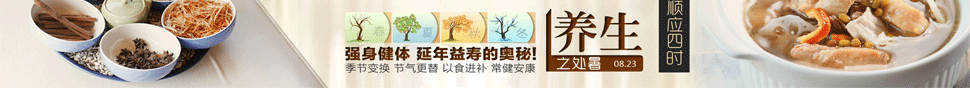
《唐诗三百首》赏析(26)
韦应物《寄全椒山中道士》赏析大历六年(公元),韦应物回到了洛阳,不久即谋到了一个河南府兵曹参军的职位。随后,他先后在河南府、京兆府做这样一个掌军防、烽驿、门禁、田猎、仪仗事物的下层官吏,直到大历十年(公元),才以京兆府兵曹参军的身份摄高陵令。后又任鄠县令、栎阳令。建中二年(公元),除比部员外郎。第二年以比部员外郎的身份出任滁州刺史。期间,大历十一年九月二十日(公元年11月5日),他的妻子元蘋去世,他亲撰并书丹了妻子的墓志铭。铭于年出土于西安市长安区,现存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。《墓志铭》中我们看到韦应物书法端秀雅健,笔法严谨质朴,绝不逊色于唐代诸书法大家。文字简洁明晰,语含深情,足见其夫妻情笃。终其余生,韦应物再无续弦。全椒山色这十年的经历,彻底改变了韦应物的人格,也彻底改变了他的生活态度,而这些改变但便促成了他诗歌创作风格的形成。凡论韦诗者,必言其为陶渊明一派的诗人。我们读《韦苏州集》,其卷一有一组“杂拟”诗,包括拟《古诗十九首》十二首、《效何水部》二首、效陶诗二首。这可能就有他“折节读书”时的习作,从中约略可以看出,他在诗歌创作上,十分注重学习汉魏以来五言诗的创作,且学习效仿者并非一家。然而促使最终走向陶渊明创作方向,应当就是这一时期的生活经历:世事的变迁,仕途的磨砺,家庭的变故,让没有了“三卫少年”的豪气——“武皇(指唐玄宗)升仙去,憔悴被人欺。读书事已晚,把笔学题诗。两府始收迹,南宫谬见推。”(《逢杨开府》)——他开始转向了追求内心世界的宁静与安谧,诗风也在这个变化中形成了。滁州任刺史的三年,是韦应物创作的旺盛时期,他一生的许多佳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创作的,如今天流行最为广泛的那首《滁州西涧》。这首《寄全椒山中道士》创作于兴元元年(公元)秋天,这是韦应物任职滁州刺史的第三年。这三年中,他公务之余,流连山水,养花种树,栽药植茶;与治内的文士、山僧、道士等广泛交往,诗酒酬赠:俨然是把自己的辖区当作了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。全椒山南屏山风景全椒县是滁州下属的一个县,今属安徽省。县内多低山丘陵,诗中所写的“山中”的山,可能是全椒县旧城南面的南冈山(今名南屏山,山内开发许多住宅小区,已非当年可以隐居避俗的处所了)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卷二十九:“(在)县南二里。山势自西来,连亘数十里,至此高峻,环绕县治,为县形胜。稍西曰黑龙山,登其山下瞰井邑,一览皆尽。有黑龙泉。”清修《嘉庆一统志》卷一三〇《滁州》:“《州志》‘(神)山在县西少北,有洞曰石门洞,深数十丈,亦曰神仙洞。可百十人。常燥不湿。相传宋南渡时,民尝避乱其中。上有小洞二,亦容十余人。然深晦不可入。曰白石洞,下有白石涧。’”二书又载全椒县境内尚有九斗山、桑根山、北独山等。(笔者没有去过全椒县,这些山峦今叫什么名字,无从知晓。)这位道士所隐居的处所,是否是这些山中的一座,也未可知。另外,道士的姓氏行状,皆无从考稽,唯有韦应物的这首诗,备受后人称道。“全首无一字不佳,语似冲泊而意兴独至,此所谓良工心独苦也。”(明凌蒙初刻朱墨套印本《韦苏州集》载桂天祥评语)今朝郡斋冷,忽念山中客。涧底束荆薪,归来煮白石。欲持一瓢酒,远慰风雨夕。落叶满空山,何处寻行迹。诗开头两句,说是因天气变冷而念及山中的朋友,“忽”似乎不是因思念或是其他任何原因,仅仅是因为天气变化,因为自己感到也郡斋里变凉了,随意地念及,这就让我们自然想到了两个人生活情趣:自然而恬淡,彼此甚至没有了感情上的牵挂。这既符合了诗人的“立性高洁”,又符合了道士的价值取向:“身心顺理,唯道是从,从道为事,故称道士。”(《太霄琅书》语)“涧底”两句,是作者想象中的道士的生活:从山涧深处采来柴禾,回到道观中煮白石而食。白石就是钟乳石或白石英,呈乳白色,中医以之入药。道家以为神仙以煮白石为粮,后成为了道家修炼的典实。这在唐诗中很为常见,如司空曙《送曲山人之衡州》:“白石先生眉发光,已分甜雪饮红浆。”贯休《古意(其九)》:“种薤煮白石,旨趣如婴儿。”贾岛《题鱼尊师院》:“夜煮白石平明吃,不拟教人哭此身。”葛洪《神仙传》有这样一则:白石生者,中黄丈人弟子也。至彭祖之时,已年二千馀岁矣,不肯修昇仙之道,但取于不死而已,不失人间之乐。其所据行者,正以交接之道为主,而金液之药为上也。初患家贫身贱不能得药,乃养猪牧羊十数年,约衣节用,致货万金,乃买药服之。常煮白石为粮,因就白石山居,时人号曰白石生。亦时食脯饮酒,亦时食谷,日能行三四百里,视之色如三十许人。性好朝拜存神,又好读《仙经》及《太素传》。彭祖问之:“何以不服药昇天乎?”答曰:“天上无复能乐于此间耶!但莫能使老死耳。天上多至尊相奉事,更苦人间耳。”故时人号白石生为隐遁仙人,以其不汲汲于昇为仙官,而不求闻达故也。那么,全椒县山中的这位道士,也是“煮白石为粮”仙人中的“隐士”了?试想一个连白日飞升这样的仙官都不愿去做的人,还有什么世间的尘嚣可以侵扰他的内心宁静呢?所以他得到的就只有人间之乐了。诗人在自己的诗歌世界中,不正是要营造一个这样的只有“人间之乐”的世界吗?
“欲持一瓢酒,远慰风雨夕”,“一瓢酒”,就是“一瓢饮”。《论语·雍也》:“贤哉,回也!一箪食,一瓢饮,在陋巷,人不堪其忧,回也不改其乐。”瓢是最简单的饮具,是贫困的代表,也是洗去繁华后的朴素。去拜访这样一位“隐遁仙人”,奢华显然是不恰当的,从诗人的生活来看,虽身为刺史,也没有什么无边的富贵。“一瓢”也是表明诗人自守清贫的生活情趣。“远慰”的“慰”字,很值得我们寻味一番。一方面时值秋季,山中的这位道士朋友,面对草木凋零,天气渐冷,也应当感到几分清苦或寂寥,携一瓢酒,去访问一下朋友,当然是对朋友的慰藉。另一方面,于作者自身,在这个秋天可能也需要一些慰藉吧。同是在这个秋天创作的另一首诗,很能说明这一点:守郡卧秋阁,四面尽荒山。此时听夜雨,孤灯照窗间。药园日芜蔓,书帷长自闲。惟有上客至,论诗一解颜。——《简郡中诸生》说到这里,我们回过来想一下“今朝郡斋冷”的“冷”字,这天气之冷中,还包含着诗人的心头之“冷”!前面我们说过诗人八年前丧偶,此时他极大的可能是带着两个未成年孩子生活。这点我们会后面的《送杨氏女》一诗详细地谈到。可见,这位从三品刺史,生活还是有些清苦的。(唐制,上州刺史从三品,中州刺史正四品上,滁州为上州。参见《新唐书》卷四一《地理志五》及《大唐六典》卷三十)诗的最末两句,写的是作者到底没有去拜访这位道士朋友。可正是这次没有完成的拜访,成就了千古名句:“落叶满空山,何处寻行迹。”满山落叶,寂寥无人,秋天的大山,更显空旷而深邃。而朋友又是一位见水止水,遇石宿石的自由散淡的道士,哪里是去见朋友的路呢?看来朋友那里是只能“神遇”了。饮酒是可以得到一时的温暖,特别是与朋友对饮。但那空旷的大山,不是更大的寂寞吗?本欲找到朋友相互慰藉,以消除这个秋天的寂寥,但去了后可能根本无法找到寻找朋友的路径。这样又会给本来已经“冷”的郡斋带来一层失望,所以干脆不如不急于去,先寄诗相问。读着读着,我们便觉得自己是在循着诗的线索脉络,做一次情感和哲理的巡行:这个看似平静的秋天,诗人的感情太过复杂了——是这首诗表达的情感和内容太丰富了,尤其是诗结尾两句,堪称是“言有尽而意无穷”的典范。宋代洪迈的《容斋随笔》记载这样一则典故:韦应物在滁州,以酒寄全椒山中道士,作诗曰:(诗略)其为高妙超诣,固不容夸说,而结尾两句,非复语言思索可到。东坡在惠州依韵作诗寄罗浮山邓道士云:“一杯罗浮春,远饷采薇客。遥知独酌能,醉卧松下石。幽人不可见,清啸闻月夕。聊戏庵中人,空飞本无迹。”刘梦得“山围故国周遭在,潮打空城寂寞回”之句,白乐天以为后之诗人无复措词。坡公仿之曰:“山围故国城空在,潮打西陵意未平。”坡公天才,出语惊世,如追和陶诗,真与之齐驱。独此二者,比之韦、刘为不侔,岂绝唱寡和,理自应尔耶?(卷十四)施补华分析其中原因说:“《寄全椒山中道士》一作,东坡刻意学之而终不似。盖东坡用力,韦公不用力;东坡尚意,韦公不尚意。微妙之旨也。”(《岘佣说诗》)也是很有道理的。其实喜欢这首诗,特别是最末两句,岂止坡公一人,但都没有追和者,大概是东坡追和没有成功,他人更不最再做尝试了:“盖绝唱不当和也。”(许顗《许彦周诗话》)最后说一下诗的押韵。这首诗的韵脚字是:客(kè)、石(shí)、夕(xī)、迹(jì)。今天读起来已经完全不押韵了。我们看一下《广韵》中对这四个字的注音情况,它反映的基本就是唐朝的汉语语音特征。寄全椒山中道士00:35来自字说心与客:苦格切,溪纽陌韵;石:常隻切,床纽昔韵;夕:祥易切,邪纽昔韵;迹:资昔切,精纽昔韵。依《广韵》,陌、麦、昔三韵部同用。既是同用,说明它们当时是可以通押的,也就是说这三个韵部,韵母虽不相同,但它们有着共同或相近的韵腹和韵尾,只要不做细致地语音学分析,在诗歌中押韵是没有问题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