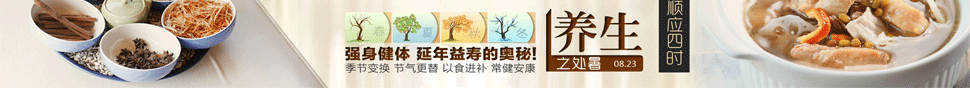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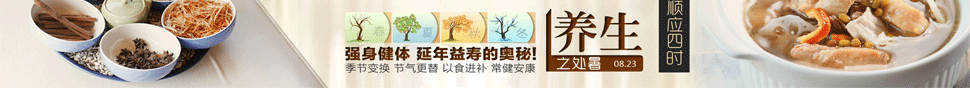
兵团二、三事
陈稚文王枰
.6.23
我们依然怀念那片白茫茫的盐碱地。骨子里,其实都是在怀念我们撒播在那里的青春年华。
我们为共产主义挖银河
摸田
连长
干涸的河道
“阿蒙”的命运
我们为共产主义挖银河
“水利是命脉,我们为共产主义挖银河!”营部的“战斗报”上用大字书写着。
东片由海涂围垦而成。盐碱土养淡,日常生活吃喝拉撒、生产经营物资运输,均离不开沿塘的河道。随着兵团建立,人员增多,生活、生产资料的需求自然直线上升。东片对外不通公路,所有交通运输工作都依赖河道进行,故唯一的老塘脚的河就更显得重要。由于农场前期的基础建设没有跟上,老塘河在九连(原新村大队)断了头。于是,兵团成立后,挖通老塘河、贯通东片水系成为第一大事。
年底,老塘脚河南段米的河道新挖、北段老河道的疏浚加深工作,在冬闲时节全面铺开,具体工作由沿河各连队分段负责完成。
河道疏浚的程序是先在上游关闸,下游筑坝放水,再用抽水机抽干积水,裸露出河道底部的淤泥。河道里长期积累的淤泥深达米余,需掏干淤泥,始可见到下面柔韧的泥床。疏浚工作就是淘干淤泥并进一步挖深河道。
海涂新挖河道是去掉土地表层半米左右的干涸的表土,即可见泥床,由于去掉表层土可以旱地操作,相对简单一些。
泥床露出后,用一种称为“泥弓”的工具把泥床一块块切割下来往河岸上传递。泥床是粘泥层,泥的柔韧性好,易切成块而不易折断;温岭农村传统的方法是,用一种类似滑板的工具,将泥块放到滑板上,用一种类似榔头的竹竿推动泥块往河岸上滑传,节省人力,效率较高。但兵团里没有这种工具,便只好用人由河底向河岸排成一列,用手将泥块一块一块往河岸上传递,打的是最原始的“人海战役”。
一营驻地在东片南,河道完全新挖;我们二营驻地是老农场加原新村大队,需新挖的河道不长,工作以疏浚老河道为主。
在十七团一、二营所有知青中,挑河的“冻”是刻骨铭心的。
正是严冬时节,每天的气温都在0℃左右。连队事先做了战斗动员,有不少知青在动员大会上宣读决心书。食堂也准备了姜汤热水。
最困难的是淘干淤泥这一步工作,湿漉漉的淤泥既不能用竹筐挑,又无法用手传递。只好用脸盆一盆一盆往上舀。
连長带领几个男知青跳入淤泥淹没到胯部的河底,先是用脸盆奋力舀干污泥,然后再用“泥弓”切割下一块块柔韧的泥块。其他知青则排成几列,用手或脸盆、将泥块一盆一盆、一块一块逐个往河岸上传递。
河底排列的是男知青,河岸往上则全部由女知青承担。挖河的工地,没有一处遮风的地方。站在光秃秃的河岸边,凛冽的海风寒冷刺骨,不管穿上多少衣服都挡不住寒冷的侵蚀,大家的脸都冻成青紫色,牙齿冻得咯咯直打颤;每个人的衣服都沾满了泞泥,手脚僵硬……
冻僵的手,根本抓不住冰冷柔滑的泥块,力气大一点的人,传递过来的脸盆、泥块接住马上就转递出去,力气小的女知青可就苦了,一接不住就掉到地上,不一会儿身边就堆积成一堆。等到别人休息时,也不能休息,还要将身边的泥堆搬掉。
下工后的姜汤热水,其实起不了作用,拚的是意志和体力。
超强的体力劳动加严寒,二排那位身体羸弱的女知青晕倒了,一排年纪最小的女知青忍受不了寒冷抱着姐姐哭……
临结束的那天,恰逢冷空气南下,天寒地冻,北风凛冽,阴沉沉的天不时飘下几朵雪花,河底结了一层薄冰,踏上河岸散落着的泥块,也是咔嚓咔嚓作响。指导员、连长、连队里所有参加挖河的战士们在阴沉沉的天幕下,像个泥人,用冻得僵硬的手传递冰冷的泥块,哆嗦着冻得打架的嘴唇,嘶声唱着革命歌曲、毛主席语录歌,互相鼓励,竭力比拚。
当连长宣布挖河战斗胜利结束时,河堤上下一片欢呼。我看到我们排那个最小的、冻僵成象个泥塑的女孩,也咧开了嘴巴在笑。在她那僵硬的脸上挤出笑意的眼睛里,分明含着两颗晶莹的泪珠。
摸田
从杭州、宁波来的知青,大概从来没有听说过“摸田”,也不知道“摸田”为何事。
“摸田”相当于旱地除草松土工序。水稻种下去后,要摸三次田,人扑跪在带有浅水的稻行间,一手支撑身体重量,一手伸展五指将稻行间的杂草清除、并把稻株周边的污泥松一松。当地农民有一个极其生动形象的比谓:“四脚爬爬象乌龟”。
第一次参加摸田,看到排长径直走进稻田扑下身去,一边示范,一边讲解。不少战士心里真的惊倒了:农田里还有如此原始的一道工序!
因为水田里除了污泥就是水,摸田时男同胞基本都是短裤上阵。女同胞则有些穿長袖衣裤,但都要高卷裤腿和衣袖。水稻叶子边缘呈锯齿状,划伤皮肤是常有的事。
南方的稻田里还生长一种水蛭,卷曲着绵软的身躯,靠拢人体就会粘上去吮吸人血。如果被粘上了,须得等待其吸饱,浑身变得膨胀圆鼓才会自动跌落,其间用力拉是无法拉下来的,只能拍打水蛭叮吸的部位周围的皮肤,让水蛭自己收缩掉落。水蛭掉落后,被吮吸处鲜血直流,在战士们的眼里,它完全象童话里描写的吸血鬼。
摸田时,正是水蛭粘附吸血的好机会。往往一趟田摸下来,便会在腿上粘上几条水蛭。经历过水蛭光顾的女知青,看到水田里游动的水蛭便会感到毛骨棘然,浑身起鸡皮疙瘩。后来,随着农药的施用,水蛭也明显减少了。
更加难以忍受的是施大粪以后的摸田。这有两种情况:一是做秧田时,为了稻秧能茁壮成长,先泼大粪作基肥,然后摸田、平整、打谷芽。这时是4月份,天气比较凉,臭气不是很大。另外是第三遍摸田,时间已经到了6月份,天气很热了。此时稻株有一、二尺的高度,用大粪施追肥,粪汁粘在叶片上,人扑跪下去,大粪汁粘的人满脸皆是。加上天气热,稻株中空气不流通,在太阳的烤晒下臭气薰天。实在是精神和身体上一大考验。好在兵团土地多、人粪尿少,除了几亩试验田要求用大粪施肥外,其它都用化肥,这样的考验还是比较少的。
有女同胞回忆说:“虽然说是知青,其实也就是小学毕业,真的连生理卫生都不懂。因为性格腼腆,例假来了不好意思启口,特意穿上长裤,跟着去摸田。毕竟夏天天气热,还是让同在一起的老农发现了。搞得他也不好意思,特意转找一个年纪大的女职工出面叫我回去。当时我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,心里忐忑不安呢,后来才知道原因。有的女知青穿着拖地的长裤,拖着长袖套,不习惯跪下摸田,起身蹲着摸田。气得排长吹胡子瞪眼睛的,吼着要她们跪下。我们班的女班长风风火火赶了过来,按照排長示范的样子扑下身子操作起来,大家也都跟着了。”
摸田的情景,至今历历在目。
连长
连长嗜酒若命,尤喜烈性酒,称得上是个玩命的汉子。他患有严重的胃病,胃病发作时痛得满头大汗。但只要有酒,不管三七二十一,仍然照喝不误。有一次和知青聚餐,在酒席上胃痛发作,竟坐到桌角处,将胃部紧紧顶住桌角,依然举杯酣饮,绝不含糊。
大凡嗜酒的人,性情比较豪爽直白,连长就是这样。他平易近人,“烂人”脾性,颇得知青好感。
大概因为肠胃不好,高高的连長显得削瘦,只是毕挺的腰板和粗大的喉咙仍然显露出军人的气概。
我一直以为连长是个“粗人”。不想他不但嗜酒也嗜书,还有注意生活细节细心的一面。
年,作为批判用书,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了《红楼梦》,一时间洛阳纸贵。消息传来,书籍《红楼梦》和越剧改编的电影都成为兵团战士热议。当时,我通过熟人买到了一套书,不知怎么传到了连长的耳朵里。夏天一个中午,知青们都在休息,连长大步踏进了我住的房间,注意到其他人正在休息,马上放轻脚步,一改平常大大冽冽高声大气的风格,压低声音悄悄地向我借书。后来在约定时间,又将细心包裹得好好的书送还过来。
挑河时节,连长胃痛频发,仍然高捲裤脚和知青一起跳入河底的淤泥中。
听说连长原来服务于汽车连队,因为工作有拼劲,很快得到提升。都说“禍福相依”,正当他朝气勃发,勇往直前时,却翻了车。一次冬夜拉练,翻越某座高山时,连队中有一辆车出了故障需要支援。连长就派了一个战士去战备通讯点联系。天黑路远,山高岭峻,风急天寒,等待支援的时间漫長无聊,加上寒冷,几个人就围成一圈点上了香烟。
突然有人发现山下公路上出现一片灯火,一队汽车疾驰过来。还未等连長丢掉烟蒂,一辆吉普已经冲到面前。团長从车上跳下一叠声追问: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,为什么要拉响战备警报。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的连長一下子蒙了,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。后来才知道是派去联系的战士误发了战备警报,致使惊动整个驻防部队。虽然这只是一场虚惊,然而连長因“玩忽职守”,大好仕途一下子变得暗淡无光。
连長有3个小孩,到建设兵团时大女儿已经有连长那么高了;下面的2个孩子,小儿子则刚刚出生还抱在手上。虽然爱人受到照顾,随军安排到营小卖部当上了营业员,5口之家,或者还有老人负担吧,家庭经济不免左支右绌,仍不宽裕,经常喝的是团部糖厂酿造的低价劣质酒“糖梗(甘蔗)烧”。
前几年,听说连长病重,我认为是嗜酒引发的后遗症,--酒精中毒或者是胃病。
步入暮年的他,很难想象,一个堂堂八尺大汉如何面对自己行动不便的景象。他只能靠大女儿照顾生活,在困窘中苦度余生。
年聚会,连队里的知青议论到连长,有人提议去看望,大家都纷纷响应,但最终因故未能成行。
新年伊始,早早传来了连长亡故的消息。
将军一去,大树飘零!
连长人生中,有在部队中不怕苦累、勤奋努力的光辉一页;也有豪爽直白,平易近人深受知青敬重的一面。晚年的他大概不会想到,生产建设兵团中的知青仍然会念叨着他。
往事如烟,在踏过海涂,经历过艰难困苦生活磨练的知青心中,连长那高卷裤腿、沾满泥巴的赤足军人的憨厚形象,永远留在岁月的记忆中。
干涸的河道
为了生活上的便利,十七团在东片的连队住房都依河而建。六连宿舍就座落在老塘脚河河道南约20米的地方。宿舍东面,有一条石板砌的路直通生活水埠。所谓水埠,就是在河道边打下二根木桩,用一块4尺石板,一头搭着河岸,一头搁在木桩上铺设而成。
年年初春旱,长期没有下雨,老塘脚河干得几乎见了底,只有河道中央还剩下约4、5米宽、30来公分深的河水。由于河道干涸,人在石板水埠上已经够不到水面,有人就从石板水埠往河道中央方向扔下几块大石头,这样一来,人可以从水埠下去站到石头上舀水、洗衣服等。
然而就是这看上去半干涸的河道,却溺死了女知青s!
溯s蒙难之源,无论是今天或35年前的昨天,我们不得不套用一个老章法:“说来话长。”
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,东片农场中部建立了集体知青点新村大队,温岭各地一些知青开始在那里垦荒种植。
s是年年底来到新村大队的。
她是一个很平常的女孩,除了与同年龄女孩相比身材瘦小,讲起话来低声小气外,说不上有什么特征。大概只是做起事来虽然小气薄力却认认真真一丝不苟,才算是她的特点吧。
虽然我曾经和她同在同一小队待过几年,说来惭愧,却是因为她的平常,使我绞尽脑汁也回忆不起她的音容笑貌。更遗憾的是,在收集新村知青相片准备做一本纪念相册的今天,她也成了人中少数几个没有找到相片的人。
集体知青点并没有规章制度,却有不成文的规定,农忙时节不能请假,农闲时也需要请假得到批准才能回家。
那时东片农场还没有通公路,回家最简捷的路程是:一大早起来,沿老海塘步行约1小时到永安,搭上汽船到新河,然后再转汽船继续走回家的路,不管是城关、温峤、还是泽国,大致上都要化一天的时间。
老海塘长满了芦苇,两侧不时可见坟茔,有些坟茔年久坍塌,甚至可以看见里面破碎的棺木和白骨。漫无边际的路上很少看到人影,孤身一个女孩子是无人胆敢走的。每逢回家,不敢独自行动的女孩子总要约几个男知青为伴才敢一起上路。
m是她的同乡,一个孤儿,生有一双棕色的眼珠,乍看起来似乎永远带有一种深沉忧郁的色彩。m待人诚挚体贴,颇得队友称道。
m酷爱唱歌,一张口,高音裂帛,绕梁三日。以高、尖、长夺冠。尤其对《马儿呀,你慢些走》这首歌情有独钟,一来劲,不管什么场合,轻快欢乐的歌声便会裂帛而出,至今新村大队少有人忘怀。队友高君便有一首打油诗描写这一幕往事:
仲夏之夜来乘凉,xx唱起“马儿也”,
歌声响彻新村队,从此雅号传至今。
m其实是他的绰号,至于他的大名恐大多人不熟悉了。
因为m的朴拙随和,经常会成为s回家的同伴。
漫长的河道、潺缓的水流倒映着白云青天;两岸的水田、树木变换着春夏秋冬;小小汽船单调的柴油机轰鸣声、窄小的船舱、寂寞的旅程……
真象一首歌中写的: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……倐忽间便流过了4年。
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十七团成立后,年“整编”了新村队,新村队的知青们被编入十七团二营各个连队,s被分配到相距3公里外的六连。m和我则留在原地、被改称为九连的新村队。
在我的记忆中,从此便没有再遇见过她。m当然也绝对没有想到过,这样的3公里距离竟然会是人天永隔!
人生的路似乎就象深邃宇宙中的两条射线,有时平行,有时交叉,然后各自走向浩瀚苍茫的星海。偶然的平行与交叉,也许只是冥冥中的注定,只是为了给人留下心底的一丝回忆。
年春节,假满后回到连队的s,黄昏到河边洗衣服时不慎失足落水。
说起来谁都会感到奇怪,河水其实不到30公分!她是失足迎面扑倒的,当用手向下支撑想抬起头时,由于河底积有厚厚的淤泥,手越用力,上身就陷得越深……
听到动静的战友们闻讯奔过去施加救助,但将人拉上岸时,s已经断了气。
温岭民间有一句俗语:“砚台里的水可以淹死人。”我一直以为未免太过夸张。当我来到s溺水的水埠、面对干涸的河道、看到河道中的泥浆痕迹时,真是无语了。生命是如此脆弱,不满盈尺的积水确实也可以淹死人的!
老队友们纷纷从各连队赶來,3队老贫农队长站在我的前面,对着河道呼唤着s。苍凉的声音在春寒料峭的旷野里迴荡……
纪念新村大队成立43年,新村知青们又聚集到一起。茶话会上,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下,m又唱起了“马儿呀!你慢些走哎慢些走……”,原来轻快欢乐的歌声变得深沉、缓慢而充满思恋,似乎又将知青们带回到35年前,带回到哪个寒冷的初春……。
“阿蒙”的命运
年出生的“阿蒙”,年加入上山下乡队伍,15岁便成为“知青”,插队到温岭东片的知青点新村大队,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。
“阿蒙”出身一般,身高一般,衣着一般,化钱一般,劳动一般,学习恐怕一般也谈不上,从来没有看到过他认真读过书。在新村大队、在连队,“阿蒙”只是个循规蹈矩,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做的好人。我戏称他为“吴下阿蒙”,寓意其不喜学习。
有一年夏季,棉花发生病虫害,由一位贫农队长带了3个知青去治虫,喷洒一种叫“”的农药,“阿蒙”即是其中一个。
“”学名叫“乙基对硫磷”,为德国拜耳公司生产之广谱有机磷杀虫药,剧毒,有一股浓烈的大蒜气味。可以通过吸入、食入、皮肤接触吸收等各种方式进入人体。如果短期内大量接触,会引起急性中毒。所以在农药瓶上标有剧毒危险标记,一个骷髅头骨形象,以随时提醒使用者要做好防护措施,防止中毒。
喷洒的过程是:将稀释的药水灌装进喷雾器,然后将喷雾器象背包一样背在背上,左手摇压喷雾器把手,使之内部增压,右手拿喷杆对着棉花喷洒雾状药液。
带班的队长完全没有农药知识,“阿蒙”对此也是一窍不通。只是遵规蹈距跟在队长身后,队长怎么说就按照怎么做。
看到棉花地里害虫又壮又大,队长担心按规格配比的稀释液治不死害虫,擅自增加了3-5倍的药量。“阿蒙”自然严格遵照执行。
天气又闷又热,灌满药水的喷雾器在背部晃动不断溅出药水浸透了衣衫,口罩里外湿漉漉的,分不清是汗水还是药水,可想而知,在这种情况下,喷洒的人完全在药水和气雾的包围下。参加治虫的4个人在毒日头曝晒的棉花地里喷洒薰蒸了一天。结果一下工,贫农队长和“阿蒙”就出现了头痛、呕吐、流涎、肌肉震颤等中毒症状。其余2人则头痛、纳呆而不适。
大队里赶紧派人抬送队长和“阿蒙”去七、八里外的农场医务室抢救。我至今还记得当时的情景:2人躺在医务室木板床上,处于半昏迷状态,不停地抽搐、呕吐,呕吐物沾染胸前衣物,地面一塌糊涂。队长,一个粗壮魁梧的汉子,眼泪鼻涕流了一面。半昏迷状态的“阿蒙”则一直抽搐、呕吐,最后甚至从口中呕吐出蛔虫来(不知是不是蛔虫也受不了农药的毒性和气味?)。在农场的医务室初步紧急处理打了解毒针后,赶紧将医院。医院恢复出院。
“阿蒙”后来随着新村大队被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独立十七团接收而编入二营。
进入兵团后,不管是组织管理、农业技术、农药安全做得都比集体知青点规范多了,再也没有出现过农药安全事故。
当然,“阿蒙”仍然是个循规蹈矩,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做的好人。没有听到过对他的表扬,没有听到过对他的批评,也没有发现他有什么特长。他默默劳动,默默生活,似乎从来没有引起过别人的注目。
大凡年青人在生活迷惘时总喜欢问:我将来会怎么样?
年夏,双抢过后放假几天,归队的“阿蒙”来到我的寝室,告诉我他曾利用假期去找一位算命大师算命,大师预言:“你不是种田的料,今年(甲寅)年底转运即可离开农村。”
那时还没有回城之说,我心里质疑大师的预言,但是看到“阿蒙”兴高彩烈的样子,又不忍拂了他的兴头,便将怀疑二字咽回肚里。
年元旦放假完了,回家的战士纷纷回连,回连的人员中不见“阿蒙”的踪影。我疑惑一向循规蹈矩的他怎么会逾期不归?
又过了几天,“阿蒙”回到连队,拿出了“特照”调令。当时,国家在知青政策上开始松动,制订了“家中父母年老,身边无子女照顾的,可以从去农村的子女中抽调一人回城”的条例。该政策在年底下达到温岭,他的老家所在地区在元旦过后率先执行。“阿蒙”在元旦放假期间得知了该信息,并在政府恢复上班这几天,办妥了手续。
我庆幸他回到了父母身边,却又隐隐担忧,身无一技之長的他,回去后能做什么呢?他坦然:“还有比零下5度,跳入河底的污泥中挖河更苦的生活吗?”他接着说:“既然我不是种田的料,哪怕是块木头,总会找到有用的地方吧。”唐.元稹诗云:“曾经沧海难为水”,“阿蒙”竟得其真谛矣!同时我心头又悚然一惊:虽然是过了元旦,按照农历现在还是甲寅年呢。“今年年底转运即可离开农村。”大师竟会是如此灵验!?
年年初,他受“特照”离开兵团回城。不久,只有小学学历的他被安排到卫生系统,经过几年磨砺,成为了一名医生。
年前后,我曾因病探访并咨询过他,他从病因分析,治疗方法到日常注意事项,侃侃谈来,有条有理,头头是道--真是非昔日“吴下阿蒙”了。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

